【春庭】
暮春的雨丝斜斜划过竹帘,在茶席上织出半透明的罗纱。我独坐在老宅的廊檐下,看铜壶嘴溢出的白烟与雨雾缠绵,恍惚间竟分不清壶中沸腾的是水,还是被春色融化的云。那只南宋建窑的兔毫盏卧在榆木茶台上,釉面流转着八百年前的天光,裂纹间沉淀的茶垢,是岁月写就的密语。

茶针挑开普洱饼的瞬间,沉睡的陈香骤然苏醒。茶刀沿着紧压的纹路游走,像是剖开被时光封缄的信笺。二十年的光阴在蒸汽中舒展成褐金色的蝶,落在盏心漾起涟漪,惊动了茶海上倒悬的春山倒影。忽然懂得陆羽在《茶经》里说的"茶性俭"——原来最奢侈的享受,恰是这般清简的郑重。
【器韵】
茶柜深处藏着祖父的紫砂壶,壶身包浆温润如古玉。记得幼时见他执壶分茶,壶嘴三点成线,茶汤总在空中划出完满的弧。壶底铭着"松风竹炉,提壶相呼",如今摩挲这八字,指尖竟触到江南梅雨季的潮湿。去年在京都古玩市集觅得一只朝鲜高丽青瓷碗,冰裂纹里沁着茶色,像冻住的海波。异国的匠人大概不会想到,这只茶碗会在中国的春日下午,盛住整片龙井茶田的晨雾。

最妙的还是那只锡制茶则,清末闽南匠人錾刻的缠枝莲纹已然模糊。量茶时金属与瓷罐轻叩,叮然声响惊醒了茶则里沉睡的往事——那些顺着海上茶路漂泊的岁月,那些在船舱里与咸涩海风抗争的茶香,此刻都化作掌心的重量。
【水相】
煮水最宜用老铁壶。经年累月的水垢在壶内结成钟乳石般的奇观,这是独属于茶人的地质年轮。看着水面从"蟹目"到"鱼鳞",再到"涌泉连珠",恍若目睹生命的三种形态:初生的悸动,壮年的舒展,归寂前的圆满。
某年深秋在无锡惠山汲泉,竹舀触破水面时,惊散了泉眼上栖息的光斑。那日的二泉水煮出的碧螺春,竟真如古人说的"有金石气"。后来才明白,所谓好水,原是能照见本心的镜子——虎跑泉泡龙井显其清,趵突泉沏普洱彰其醇,而故乡井水里的粗茶,最解离愁。

【光阴】
茶席上最动人的,是那些被茶烟熏染的停顿。等水沸的须臾,看茶针在饼茶上雕刻年轮;出汤的间隙,数着建盏里浮沉的茶毫;品饮的留白,任舌底的甘韵攀上眉梢。这些细碎的时光切片,在电子钟表的数字洪流里,是格格不入的奢侈。
记得在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见过唐代煮茶场景复原。那些被碾成翠末的茶粉,在银茶鍑里翻滚如春江潮水。今人总嫌古法繁琐,却不知当茶杓击拂出"雪沫乳花",陆羽们正在完成对时间的驯服——将焦灼的等待,熬煮成诗意的仪式。
【禅机】
日本茶道讲究"和敬清寂",中国文人却更爱说"茶禅一味"。在景德镇拜访过一位做茶器的陶艺家,他的茶室墙上悬着"吃茶去"的墨宝,地上却散落着智能手机与蓝牙音箱。见他从容地在现代与传统间摆渡,忽然懂得:所谓茶道,原不在形制,而在那杯茶汤映出的本心。
深秋夜雨时读《茶之书》,读到千利休说"茶汤无非是烧水点茶而已",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清澈。起身用玻璃杯泡了袋装绿茶,看嫩芽在沸水中舒展如初,竟也觉出三分禅意。原来茶道的至境,是能于纷繁中守拙,在急促里得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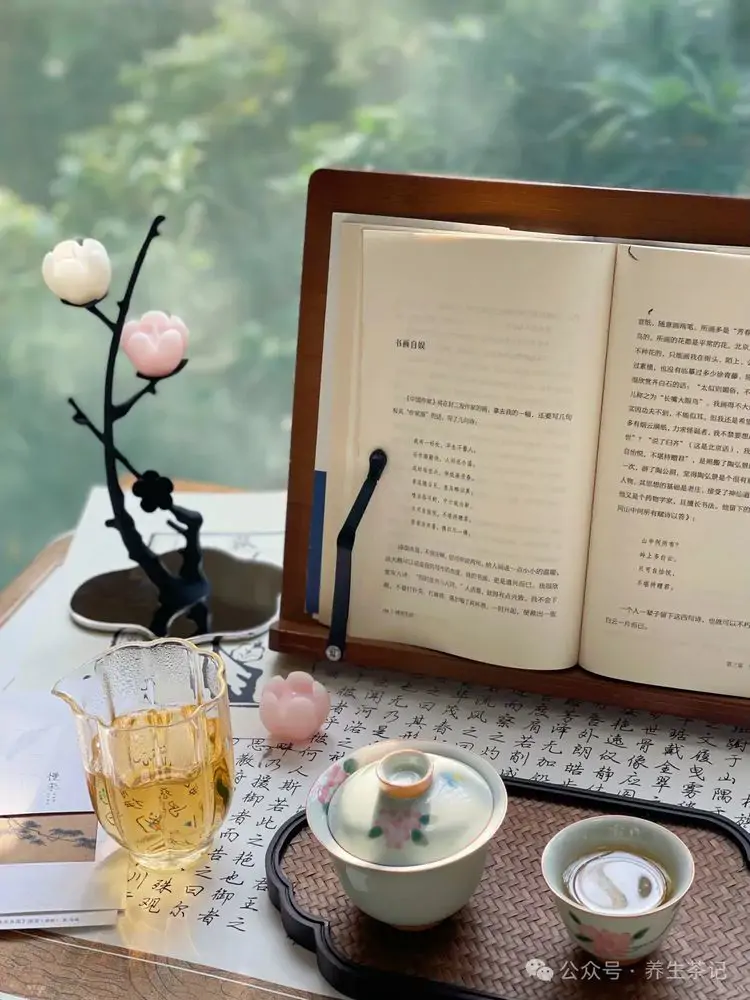
【余韵】
暮色漫上茶台时,最后一泡茶已淡至无味。建盏底残留的茶渍,在夕照里泛着琥珀色的光。收拢茶具的动作总比展开时缓慢,像是在为一场仪式书写尾声。铜壶渐渐冷却的嗡鸣,紫砂壶盖上凝结的水珠,还有茶巾上晕染的淡黄痕迹,都在诉说着未尽的余韵。
想起在云南景迈山见过古茶树的采茶祭。布朗族老人将新茶撒向千年茶树王,吟诵声与茶香一同飘向云海。
此刻方知,当我们闲坐喝茶时,啜饮的不仅是草木精华,更是天地人间的某种永恒契约——以片刻清闲,换得灵魂的吐纳;借一盏春色,窥见生命的本真。